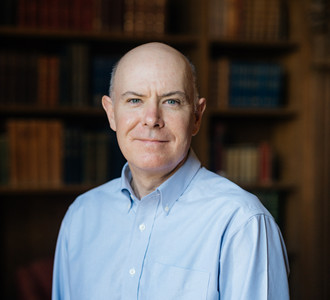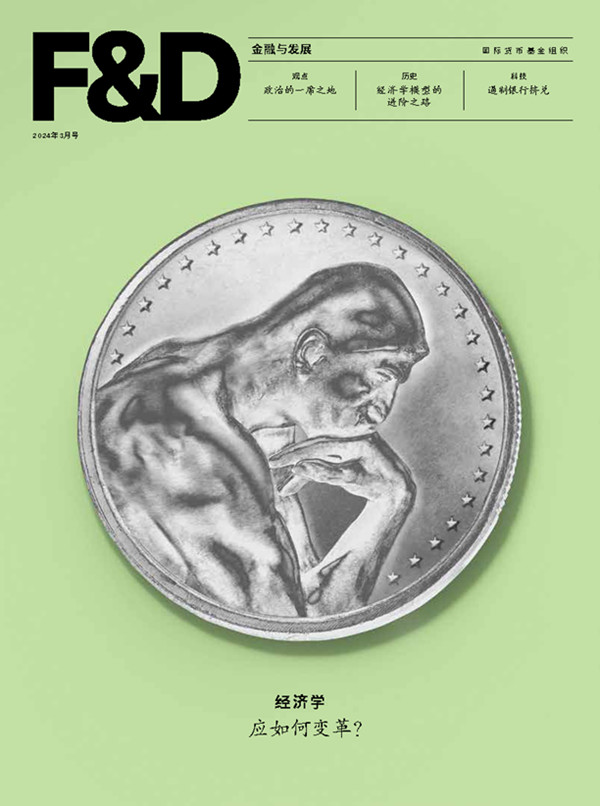发展中经济体是否应当效仿美中,兴建国家龙头企业?
地缘政治正在迅速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短短几十年前的政策环境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改革时期,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开放市场,拥抱全球化。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建立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非歧视贸易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专注于经济增长,俄罗斯则疲于维持稳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暂未显形。
如今,政策制定者们则在争论全球化的未来。他们担心世界经济出现割裂,全球贸易规则成为一纸空谈。贸易干预正在增加,其形式包括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国家安全和环境问题为由的进口限制,以及旨在惩罚地缘政治对手、确保国内供应的出口管制。
发展中经济体要如何应对这种新局面?它们是否应当采取类似的、内顾型的政策,通过补贴和贸易管制来保护关键产业?
关于发展中经济体是否应当参与世界经济,这一争论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许多观察者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前景持悲观态度,担心它们的贸易条件会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力量被认为加剧了不平等、将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推向落后的深渊。人们那时认为,需要出台进口替代政策,使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上更加自力更生,减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
误读历史
有关国家之所以实施内顾型政策,部分原因是对历史的某种特定解读。它们认为,富裕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保护了制造业——这种看法令产业政策受到了青睐。事实证明,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尽管关税很高,但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基于其开放经济体(移民开放、资本开放、技术开放)的定位,并且拥有体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此外,19世纪末,征收高关税的美国通过提高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人均收入方面赶超了采取自由贸易的英国(Broadberry,1998年)。在西欧,经济增长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有关。旨在保护农业免受低价影响的贸易政策,可能是导致德国等国延迟发生这种转型的根源。
虽然全面的进口替代在几十年前已不再受青睐,但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又为它镀了一层金,但对于这个问题,标准的历史也可能具有误导性。1960年,韩元币值被高估,出口仅占GDP的1%。韩国的进口能力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援助。20世纪60年代早中期,货币贬值后,韩国的出口竞争力得到加强,呈现爆炸式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初出口已达到GDP的20%。其主要政策包括设定一个现实的汇率,为出口蓬勃发展创造机会,同时为所有出口商(而非目标产业)提供更低廉的信贷(Irwin,2021年)。直到1973至1979年的“重化工业大发展”运动期间,韩国的产业政策才真正兴起,而该运动因成本过高、效率低下而被最终叫停。但在产业政策时代之前,韩国已显露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一直呈胶着状态。一些人认为它是生产率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推手,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助长了腐败、降低了效率。一些人以阿根廷斥巨资在火地岛兴建电子产品组装厂为反例,但另一些人以中韩两国的高科技工业蒸蒸日上为正面教材。产业政策的效果很容易被夸大。定量模型表明,即使是最优化的产业政策,其带来的收益也很小,且不太可能带来重大变革(Bartelme等人,2021年)。
最新情况是,继中国之后,美国也开始明确支持产业政策。中国这么做至少可以追溯至习近平主席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远离了邓小平及其后领导人秉持的外向型政策。包含大力补贴目标产业的“中国制造2025”纲领,已经让位于“双循环”理念,其注重通过加强本土企业的国内采购来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推动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保护钢铁和铝行业。通过《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美国对企业推动半导体生产的“回流”提供补贴,并对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实行国别限制,以保障国内生产。欧盟一直有产业政策,其曾于2020年宣布过一项产业战略,在向绿色和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加强“开放战略自主权”。
发展中经济体要何去何从?是否应当效仿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新共识,通过政府补贴和贸易限制大力扶持特定本国产业?这项战略的风险很大。补贴可能所费不赀,但效益却不甚明朗。贸易限制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内向型保护主义,导致出口收入减少,对关键进口产品的购买也会相应减少。
大规模的产业补贴恐怕是富裕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美中欧能够负担补贴,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应当效仿。里卡多 • 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的警告不无道理:“一味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却不管本国是否存在相应问题,或者只着眼于最近流行的问题,却意识不到它根本不重要,这些都是效率低下甚至祸国殃民的做法。”受财政困扰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财政收支不稳定、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切忌过度补贴国内生产。公共资金本就稀缺,若用于改善卫生和教育、帮助穷人,其效果要比直接投入国内产业更好。
产业补贴,进口替代
中国的例子说明了产业补贴消耗稀缺资源,效率低下。2006年,中国将造船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开始大规模生产,并通过低息贷款等措施给予投资补贴。有证据表明,这类政策不仅没有产生显著的效益,反而造成了浪费(由于产能过剩)和市场扭曲(迫使效率更高的国家进行相应调整,减少产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增长,以牺牲日韩欧的低成本生产商为代价,但其国内生产商并未获得可观的利润(Panel、Kalouptsidi和Bin Zahur,2019年)。由于低效率的生产商一窝蜂涌入,补贴被瓜分一空,引发产能过剩、产业割裂加剧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贷款极具政治色彩,获得大力扶持的都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效率更高的私人企业。造船业并没有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也没有证据表明整个行业在实践中学习进步。
牺牲贸易收益
另外,转向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发展中经济体损失一部分从世界市场中获得的收益。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取得经济进步,依靠的是投身全球经济,而非以刺激本土创新为由关闭市场。中国致富靠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进入制造业和释放私人部门的潜力。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废除了扼杀私人企业的“许可证制度”的繁琐程序,开放了经济,这一举措至今仍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改革还不够彻底。孟加拉国也因向外国开放投资而受益匪浅,大量资本与技术流入,令其人均收入超过了印度。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经济交往带来的利益都要超过经济孤立,因为它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技术和投资。
尽管贬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成为一种时尚,但改革时期的开放令全球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而非历史常态中的逐渐扩大。从1990年左右开始,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逐渐向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水平看齐(Patel、Sandefur 和 Subramanian,2021年)。
近期关于全球化是否已死的争论尚无定论。发展中经济体若是背弃全球经济,放弃支持出口,不再从国外获取技术,那么这种做法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它们仍然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许多利益,但如果重回闭关锁国的状态,它们将面临很大的损失。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