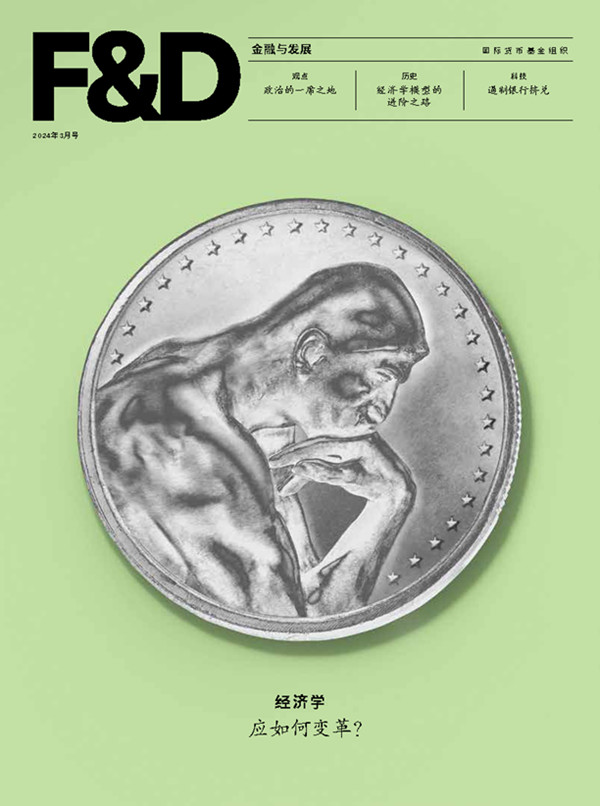多年来,处置不当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其他灾害侵蚀了青年对于政治家的信任
失去了信任,政界人士就很难说服民众听从自己的建议和指示。从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再到当前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危机,政府一直要求或告诉民众要改变行为,要做出牺牲——在战争情况下要做出巨大的牺牲。然而由于阴谋论甚嚣尘上,要建立并维持信任正在变得愈发困难。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于疫情的反应突显出信任的重要性,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可以引以为戒。
政府和现代医学为缓解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官员和公共机构提出建议,发布规则,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并接种疫苗。科学工作者作为顾问为相关规则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作为研究人员开发了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现在又开发出了有望遏制疾病传播的预防和治疗药物。
近期研究和随机观察都表明,公众必须信任政府官员、科学工作者及其相关机构,这些工作才有望成功。只有民众认为政府值得信赖,相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公正无私、有理有据的,他们才有可能遵循政府发布的建议和指令。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022年初刊载了一篇研究论文,文中分析了177个国家的新冠肺炎发病率,发现民众对于政府和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感染病毒的病例数量就越少,这二者在整个研究期间始终存在统计学上的重要关联”。无独有偶,开展国别比较和个人比较的多项研究均发现,信任科学与遵守防疫措施呈正相关。由此可见,只有民众认为科学工作者值得信赖,才有可能遵循他们提出的建议和指令。疫苗怀疑论者时常质疑科学工作者的动机、能力和诚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不过,信任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经过一系列事件,逐渐磨练而成。近期研究发现,许多事件都会显著影响个人对于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的信任,其中之一便是经历疫情。对于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的信任,会因经历疫情而受到负面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表现出来的信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在一系列论文中反复指出,经历疫情对于年轻人——确切地说是18至25岁的青年人——的信任程度影响最大。
敏感年龄
众多研究发现,人在青年时期会经历认知和行为的剧烈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此后还将持续存在。社会学家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本宁顿学院的学生开展了一项经典研究,他发现研究对象在本科阶段形成的社会和政治信仰在毕业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融入了历久弥坚的个人思想认同。心理学家乔恩·克罗斯尼克(Jon Krosnick)和社会学家杜安·阿尔文(Duane Alwin)指出,人在18至25岁之间习得的政治观念和归属感往往会持续多年。经济学家保拉·朱利亚诺(Paola Giuliano)和安东尼奥·斯皮林伯格(Antonio Spilimbergo)发现,在18至25岁之间经历过经济衰退,会对一个人的经济观念产生重要且持久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研究人员将人生的18至25岁称为“敏感年龄”。
对于敏感年龄的重要性,人们有着多种不同解读。一些学者借鉴了20世纪初哲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全新接触”概念,曼海姆认为当晚期青少年走出家门,第一次接触到新的想法或事件时,会形成持久不变的观点。其他人则援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观点,他的著作指出晚期青少年和青年正处在形成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年纪,他们会欣然接受新的影响。认知学家认为,人在敏感年龄形成的观念具有持久性,这与始于青春期晚期的认知能力提高有关。还有人指出,神经学研究发现,形成持久不变的观念与青少年和成年人大脑之间的神经化学和解剖学变化有关。无论如何解读“敏感年龄”,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疫情与政治信任
我们的工作首次提出了大规模证据,说明疫情对于正处在敏感年龄的个人的政治信任造成的影响。我们采用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6至2018年间140个国家的民众对于政府、选举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年信任数据,以及非政府组织EM-DAT维护的国际灾害数据库中1970年以来的流行病发生率数据。采样周期截至2018年,早于新冠疫情的暴发时间。不过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得到了多项测试的支持。
我们发现,经历疫情会对民众对于政府、选举和领导人的信任程度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特别是在敏感年龄。在控制其他各项社会、经济和个人特点变量的情况下,我们询问在敏感年龄经历疫情的群体,与同年接受调查的本国其他群体相比,是否表现出更低的政治信任度。
经历疫情会造成巨大冲击:与未受影响的群体相比,在敏感年龄阶段始终深受疫情影响的群体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会降低5.1个百分点,对选举诚信的信任度会降低7.2个百分点,对国家领导人表现的认可度会降低6.2个百分点(这些变量的平均值分别为50%、51%和51%)。
令人不解的是,对于在疫情暴发时尚未达到或是早已超过敏感年龄的人,则没有产生类似的影响。随着受影响者的年龄渐长,这些影响会逐渐消褪,平均可以持续将近20年。
医疗卫生应对政策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发现这种影响是特别针对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警察、军队、银行和金融机构等其他社会机构没有受到类似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外是个人在敏感年龄阶段经历疫情与他们对于本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之间的关系,这里再次显现出明显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民众是否信任政治机构,与政府的卫生保健政策能否充分应对公共卫生威胁有关。
面对疫情,没有充足的立法权、不够团结、得不到民众充分支持的政府通常最没有能力做出有效的政策响应。我们比较了各国针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记录下了这一事实。2020年的证据可以证实,实力较弱的政府用了更长的时间才进行第一次非药物干预。假如这种政府确实会让选民失望,可以预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疫情暴发时在台上执政的政府软弱无力而且动荡不定,对于民众信任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达到最大值。事实上,我们发现当暴发疫情与软弱政府同时出现时,经历疫情对于民众信任的影响就会放大一倍。
最后一点,可以看出在青年是否信任政府的问题上,民主国家的民众受影响最大。我们控制了收入水平等国家特点以及多项个人和家庭特征等变量,这项研究结果是稳健的。可以这样解释,年轻人希望民选政府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当政府没能如其所愿预防或遏制疫情时,便会感到失望。此外,民主政体可能更难做到保持信息的一致性。这是由于民主政体是开放的,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官方意见,从而进一步削弱民众的信心和信任。
对于科学工作者的信任
我们采用同样的比较方法以及惠康基金会在2018年对138个国家大约75,000人开展的调查,分析了疫情经历如何影响到民众对于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信任。研究再次表明,经历疫情对于信任问题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而且同样以青年尤为突出。与在相同人生阶段没有经历过疫情的类似群体相比,曾在18至25岁之间经历过疫情的人,对于科学工作者和科学研究的裨益的信任度明显降低。与没有经历过疫情的人相比,在敏感年龄阶段受疫情影响最严重者,对于科学工作者的信任度平均偏低11个百分点。经历疫情时尚未达到或是已过了敏感年龄的人,在信任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这种变化。
我们还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组,一组只在小学阶段学习过科学知识,另一组的科学教育至少持续到中学阶段。我们发现,科学相关科目的教育背景比较薄弱者拉低了信任度。
疫情导致年轻人的信任度降低,继而对疫苗也产生了负面看法。这既影响了民众的实际行为,也影响到人们的态度。具体说来,调查问卷分析表明,在敏感年龄经历疫情会降低民众让子女接种儿童疾病疫苗的可能性。
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令人不安。我们知道,是否信任政府和科学专家,对于公众能否接受相关建议和政策意义重大。近期经验表明,这对于公众能否接受旨在减缓新冠疫情的传播和影响的建议及政策尤为重要。不过,假如传染病的暴发削弱了民众对于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的信任,就会诱发一场恶性循环——疫情暴发,信任降低,导致疫情以及各种继发危机更难遏制。
这种影响其实不限于公共卫生领域。其他研究表明,信任是决定社会如何应对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可见信任是一项长期经济发展因素。不过,假如暴发疾病削弱了年轻人的信任,可能会减损并延缓应对其他紧急事态的社会举措,并给经济发展造成阻力。观念上的这种变化具有持久性,今天的年轻人将成长为明天的成年人,这些阻力也就愈发难以克服了。
不过还有一线生机。正如我们看到,针对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应对不力的政府最易失去民众的信任。因此,假如政府能够认识到疫情风险,提前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就不太容易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一些非洲国家成功应对了新冠疫情,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艾滋病毒(HIV)等早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过后,着力增强本国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说到对于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信任,科学教育可助一臂之力。
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了一项重要差异,涉及到年轻人在经历疫情之后,他们对于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看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科学工作者的诚信、科研结果的准确性以及科研工作对于公众的裨益,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不过对于科学事业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人们是否相信科学是一项事业,是否认为科学技术有助于改善生活)。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文献中关于人在复杂的高风险社会环境中如何归咎责任的论述,人们倾向于指责个人而非机构的态度,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政界人士和评论家一面质疑个别科学家的公共政策建议是否有价值,一面积极调动所有科学资源投入开发疫苗,无不体现出这种差异。
因此,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于科学工作者该如何展示自己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人们担心科学工作者也是人,会有私心,会受到政府和企业目标的不当影响。人们还担心,科学工作者的结论是基于个人意见,而非确凿的证据。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分歧——在疫情迅速蔓延期间,这种分歧并不罕见——恰好证明了他们的结论是基于个人意见,或是表明相关研究人员的能力不足。
有鉴于此,消除人们对于企业目标和个人偏见的忧虑是很必要的。科学工作者需要做出解释,说明意见分歧以及与早期研究结果相矛盾的新证据都是科学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一部分。应对新冠疫情的公共政策突出了这种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我们的分析表明,务必要让这种沟通适合正处在敏感年龄的年轻人,以便加强信任,让社会能够为今后的大流行病和其他突发状况做好准备。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