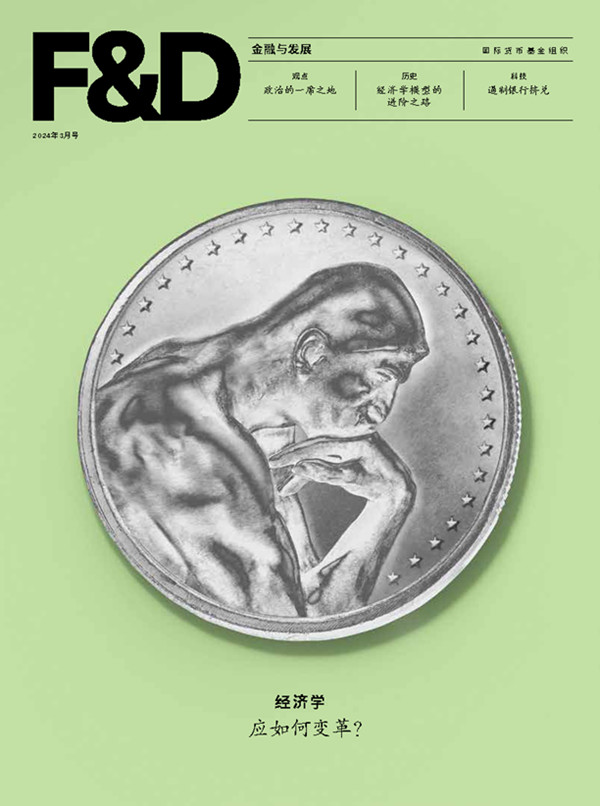观点
面对这个时代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各种务实的补救措施
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与一套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特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倾向于扩大市场(包括全球市场)的范围,并限制政府行动的作用。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做法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失败了。它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对促进气候转型几乎毫无助益,还造成了从全球公共卫生到供应链韧性等一系列盲点。
新自由主义时代确实见证了一项重大成就。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人口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极大地降低了全球的极端贫困水平。然而,在这一时期表现最好的国家(例如,中国)却几乎没有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它们对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资本管制的依赖不亚于对自由市场的依赖。与此同时,最严格遵循新自由主义“兵书”的国家(例如,墨西哥)表现非常糟糕。
经济学需要对新自由主义承担责任吗?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套政策建议。当代经济学的工具很少得出能立即提供政策指导的概括。一阶原则(例如,考虑边际情况,将私人激励与社会成本和收益、财政可持续性和健全的货币挂钩)本质上是抽象的概念,无法形成独特的补救措施。
中国本身就是经济原则可塑性的最佳例证。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中国政府利用了市场、私人激励和全球化。然而,中国是通过非常规的创新(家庭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创新在标准的西方政策建议中是不被承认的,但在放松国内政治和次优约束方面却是必要的。
在经济学中,几乎所有政策问题的正确答案都是“视情况而定”。正是在仔细审视这种环境依赖性(即经济环境的差异如何以及为何会影响结果,例如政策后果)时,经济分析才有意义。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原罪是相信一些简单、普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法则。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实际运作的经济学,那么它所展示的是糟糕的经济学。
新挑战,新模型
更好的经济学必须从下列前提出发:我们现有的政策模型不足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广泛而大量的挑战。经济学家必须充满想象力地应对这些挑战,在运用他们的专业工具时,应考虑到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差异。
最根本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在经济学家的理想世界中,解决方案是围绕一种“三管齐下”(全球实行足够高的碳价或同等的限额与交易制度、全球对绿色技术创新给予补贴,以及大量金融资源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方法开展全球协调。现实世界是由一个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不太可能交付任何接近这种最优解决方案的结果。
最近的历史表明,要想采纳绿色政策,就必须进行混乱的国内政治交易。每个国家都将自己的商业考虑至于优先地位,同时让绿色政策的反对者和潜在输家参与进来。中国促进太阳能和风能的产业政策一直受到竞争对手的嘲笑,但却大幅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都是建立在国内政治交易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然而,它们对绿色转型的贡献可能比任何全球协议都要大。如果要让这些政策发挥作用,经济学家就必须停止做最优的纯粹主义者,或者仅仅关注这些政策的效率成本。他们需要充满想象力地制定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次优和政治限制问题。
如果说气候变化是对自然环境最严重的威胁,那么中产阶级的衰落就是对社会环境最严重的威胁。健康的社会和政体需要一个基础广泛的中产阶级。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高薪、稳定工作一直是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基础。但近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处境并不好。超级全球化、自动化、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和紧缩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或者说好的就业岗位短缺。
要想解决好就业岗位的问题,就必须制定超越传统福利国家的政策。我们的方法必须把创造好的就业岗位放在首位和中心,同时关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企业和技术)以及供给侧(技能、培训)。政策必须特别针对服务业,因为未来服务业将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它们必须以生产率为导向,因为更高的生产率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获得良好就业岗位的必要条件,也是对最低工资和劳动法规的必要补充。这种方法需要对新政策进行试验——为吸纳劳动力的服务业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发展中经济体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表现为过早地去工业化。要想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并取得成功,就必须掌握日益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因此,制造业中正式就业的峰值水平是在收入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达到的,就业去工业化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得早得多。过早地去工业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它导致今天的低收入国家无法复制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当可贸易部门对技能和资本的要求很高时,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的经济增长就不再有效了。
这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未来必须像发达经济体一样,减少对工业化的依赖,而是更多地依赖服务业中的生产性就业。在促进工业化方面,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以服务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关于由非常小的企业主导的非贸易服务的发展战略,需要未经检验的全新政策。经济学家必须再次开放思想,勇于创新。
全球化的未来
最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全球化模型。分配斗争、重新强调韧性以及中美两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都对超级全球化造成了损害。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需求与国内相互竞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义务的再平衡过程之中。尽管许多人担忧新时代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未来全球环境缺乏宜居性,但是结果不一定都是坏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家经济管理受到全球规则和全球市场需求的限制明显较少。然而国际贸易和长期投资显著增长,采取了适当经济策略的国家(例如,“东亚四小虎”)尽管面对发达经济体市场较高的保护水平,表现异常出色。
今天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结果,只要大国不把地缘政治放在首位、以至于开始以纯粹的零和视角看待全球经济。在这方面,经济学也同样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经济学家可以帮助全球经济设计一套新的规则来帮助实现再平衡,而不是对过去的时代表示怀旧,因为过去的时代产生了好坏参半的结果,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可持续。尤其要指出的是,他们可以制定政策,帮助政府关注国内经济、社会和环境议程,同时避免实施明确的“以邻为壑”政策。他们可以制定新的原则,澄清需要全球合作的领域与应优先采取国家行动的领域之间的区别。
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是在贸易收益与国家制度多样性收益之间进行权衡。一种利益最大化会导致另一种利益受损。在经济学中,“角点解”很少具有最优性,这意味着合理的结果将需要牺牲两种收益中的一部分。如何在贸易、金融和数字经济中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目标,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经济学家可以对此给出更多的解释。
经济学家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加快气候转型、创造包容性经济、促进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经济学101”解决方案。他们的学科提供了比经验法则多得多的东西。只有当经济学扩大而不是限制我们的集体想象力时,它才能有所助益。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丹尼 • 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国际经济学会的前任主席。
丹尼 • 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国际经济学会的前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