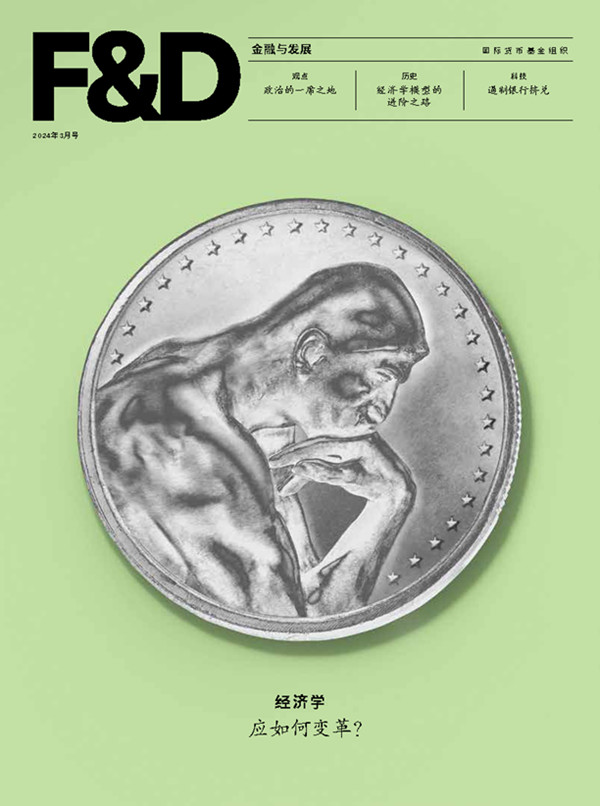现在是时候反思货币政策的基础与框架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众多教授面前,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这场危机的到来?”如今,如果查尔斯三世效仿他母亲的做法,他很可能会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次是关于高通胀的。
而从以下两点来看,他也有充分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在最近通胀飙升到40年来未见之水平之前,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一直高度担忧的是低通胀问题。其次,明明物价在快速上涨,这些央行仍自信地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抑制通胀势头。不可否认,引起通胀的主要是供给侧事件,例如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引起的贸易和生产扰动。人们认为这些事件超出了货币政策的影响范围。然而,它们对通胀的影响与先前的金融环境有关,而金融环境又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因此,对于居高不下的通胀,央行人士们并不能完全推脱过失。
正如英国女王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们提问时一样,面对眼前的危机,学术界和央行界亟待深入反思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及(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理论模型。
无根据的担忧
传统上对通缩和利率降至最低水平(或“零利率下限”)的担忧,在2020年8月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于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如果通胀预期低于我们2%的目标,利率将随之下降。接下来的后果是,遇到经济低迷时期,我们通过降息提振就业的空间就会更小,通过降息稳定经济的能力也会减弱。我们已经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看到这种不利的情况。我们也已经意识到,这种效应一旦形成,就很难被克服。我们希望竭尽所能防止美国也出现这情况。”
央行在说明其应对通胀走弱而采取的激进货币宽松政策时,给出的核心理由即是如此。这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必须通过事实来证实。仔细研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验(鲍威尔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日本),对这种解释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日本确实比其他经济体更早达到了零利率下限。如果零利率下限严重约束了政策空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低于七国集团内的其他经济体。然而,从2000年(大致是日本央行降息至零、开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时候)到2012年(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开始膨胀之前),日本人均GDP的增长率与七国集团的平均水平基本是一致的。同期,日本劳动力人均GDP的增长率处于七国集团中的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在2013年后的几年里,日本央行进行了所谓的“伟大货币实验”,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GDP的30%扩大到了120%。然而,此举在提升通胀方面的效果有限,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不大。2008年后,其他很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非常规政策,但其效果也大多不尽如人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常规货币政策总是无效的,它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威力强大的货币工具,关键在于正确的应用时机。以央行的前瞻性指引为例,通过向市场发出强烈信号、表明其政策利率的预期路径,央行可以影响长期利率。然而,当经济疲软时,前瞻性指引的效果不是很显著,因为市场参与者预计利率无论如何都将保持在低位。但如果经济受到需求或供给的意外冲击,央行延续低利率的前瞻性指引,则可能导致扩张和通胀效应过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
政治上的幼稚
央行未能更快收紧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广泛使用了具有灵活性的平均通胀目标制——这种制度明确允许通胀在短期内超越目标水平。当央行决定允许通胀超调时,它们似乎忘记了收回货币宽松政策的固有难度——而这些问题是它们的前辈们多年前曾经遇到过的。你可以自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非民选的央行人士能否要求政府和立法机构削减那些它们在选举中承诺的通胀性支出计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持续20年左右的经济平稳增长和通胀稳定(即所谓的“大缓和”时期)似乎降低了央行的警惕性。人们普遍认为在那个时期独立的央行成功实施了货币政策,但这种成功可能需要归结于不错的运气和偶然的环境。当时,全球经济受益于诸多有利的供给侧因素,如发展中经济体和前社会主义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上述因素使低通胀与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能够同时出现。那时,央行的工作不需要行使太多的政治职能。
在经历了那段宁静的时期之后,央行独立性得到了广泛的接受。随后,各国央行开始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不过,认为只要有必要,央行就能够轻松撤销政策的假设可能有点天真了。遗憾的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支持有利供给侧因素的环境正受到多个方向的攻击: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民粹主义抬头以及被新冠疫情扰动的全球供应链。目前,各国央行面临着通胀和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导致政策的撤销变得异常困难。
反思货币政策框架
当我们反思央行为何没能预测到当前这波通胀浪潮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所依赖的理论模型,然后相应更新货币政策框架。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是否应该继续专注于通缩和零利率下限所带来的风险。这个问题亟需考虑,因为它会影响央行结束当前紧缩周期的时点。有迹象显示美国通胀的高峰已过,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呼吁提高通胀目标,这样可以降低进一步紧缩政策的压力,从而保持足够的安全余地,避免通缩风险出现。
我对这个论点持怀疑态度。即使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设定了更高的通胀目标并具有更多的降息空间,全球经济的命运也不会有很大不同。我同意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观点,他被人们认为终结了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的高通胀:“通缩是金融体系严重崩溃带来的一种威胁”。他准确总结了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验教训,而我们在2008年及时采取了措施,避免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关键区别在于,2008年防止金融体系崩溃的努力更加有效。
如果金融失衡表现为债务引发的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那么额外的降息空间不会带来任何慰藉。因此,央行不仅必须关注通胀和产出缺口等宏观经济形势,还要关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变化。
其次,我们必须反思央行为何被迫实施长期货币宽松政策,以及其后果是什么。以日本为例,结构性因素(尤其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减少)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曾被误判为周期性疲软。这导致了持续数十年的货币宽松政策。但这并不等同于认为降低利率是对自然利率下行的响应。相反,对于那些需要更为根本改革的结构性问题而言,货币政策成为了一种权宜之计。
奇怪的是,有关货币政策的讨论通常假设货币宽松和紧缩政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交替出现。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货币宽松政策只影响需求侧”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若货币宽松政策持续更长时间,比如10年甚至更久,那么由于资源错配而对生产率增速的不利影响会加重。货币政策当然不应以供给侧因素为导向,但也不应忽视这些因素。
各国存在的差异
最后,我们必须关注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框架方面的差异。例如,企业雇员方面的不同做法会产生不同的工资和通胀动态。在日本,消费者通胀虽然在上升,但增速要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文化所致:在日本,企业员工(尤其是大企业员工)受到一项隐性契约的保护,根据该契约,老板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裁员。正因为如此,企业老板对于未来的增长预期持谨慎态度,通常只有在对未来真正有信心时才会给员工提供稳定加薪。这对通货膨胀有抑制作用。
即使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社会契约或经济结构的差异也有重大影响。这削弱了使用一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通胀目标制的理由。我们必须牢记为何我们没能找到一种比弹性汇率制更好的替代制度: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宏观经济偏好,这种差异通过各国货币的涨跌得以体现。货币的锚定(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只能通过央行的坚定承诺来实现,这包括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并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非仅仅设定通胀目标。
通胀目标制本身是一种为应对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严重滞胀而出现的创新。没有理由认为它就必须是一成不变的。考虑到其所展现的局限性,现在正是时候重新思索我们过去30年所依赖的理论体系,更新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