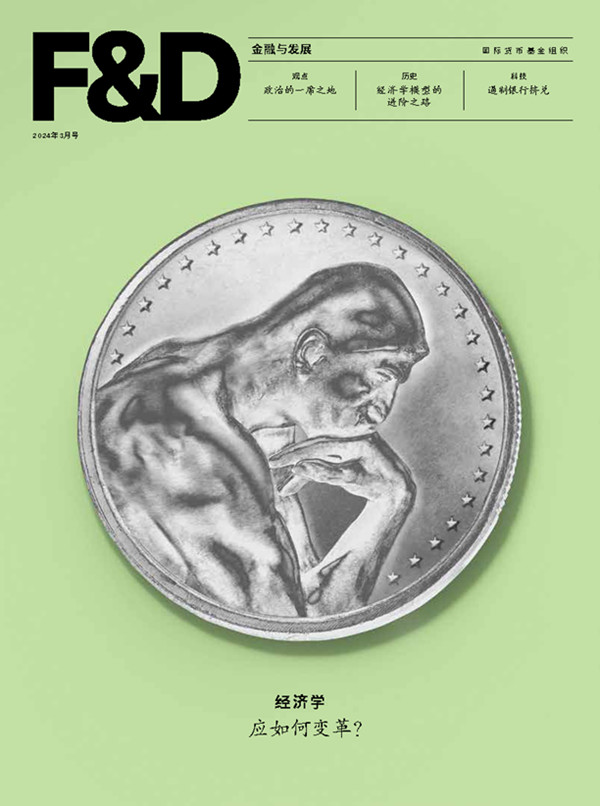如果央行突出重点、减少干预,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工业化国家的央行官员在民众当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被视为救世英雄,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支撑着微弱的经济增长,允许劳动力市场稍稍过热,从而促进少数群体就业,努力遏制气候变化,同时还严厉斥责无所事事的立法机构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可现在,人们指责这些央行官员就连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做好——保持稳定的低通胀。政客们嗅到了血腥味,他们不信任非民选的权力,希望重新审查央行的职能。
央行完全做错了吗?如果做错了,那么它们应该怎么做呢?
为央行辩护
我首先要说说为什么不应苛责央行。当然了,事后诸葛亮总是好当的。但这场疫情前所未有,它对全球化经济产生的影响很难预料。由于立法机构两极分化,他们无法就将谁排除在财政救助之外达成一致,这也许使得财政应对措施过于慷慨,而且不易预测。人们也没想到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会在2022年2月发动一场战争,进一步扰动供应链,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
毫无疑问的是,央行对于日益明显的通胀迹象反应迟钝。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世界依然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环境中,每一次价格上涨——哪怕是石油价格上涨——都几乎不会影响整体物价水平。为提振过低的通胀,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甚至改弦易辙,宣布将减少对预期通胀的反应,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套做法对于存在结构性低需求和低通胀的时代是适用的;但在通胀即将大幅上升,每一次价格上涨都将引发另一轮价格上涨之际,采取这套做法却是大错特错。但谁又能知道时代正在改变呢?
即便有先见之明,央行仍可能落后于时代——这也难怪,它们其实并不比那些能干的市场参与者更了解实际情况。央行遏制通货膨胀的办法是放缓经济增长。央行的政策必须被认为是合理的,否则就会丧失独立性。此前,各国政府为支持经济增长耗费了数万亿美元,熬过了可怕的就业低点,刚刚恢复了些元气,而通胀水平也在过去十几年中低得几乎让人注意不到;在公众还没有看到通胀危险时,只有鲁莽的央行人士才会冒冒失失地提高利率,破坏经济增长。换言之,先发制人地加息会放缓经济增速,这在公众看来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如果加息达到了目的,后续没有出现通胀加剧,就会显得格外不合理;假如能给公众带来幸福感的泡沫金融资产因加息而贬值,情况就会变得更加不合理。央行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通胀,就必须先让公众看到通胀在上升。
总之,央行受制于很多因素,不能随意行动——近代史的发展、央行的信念、为应对低通胀而采用的整体框架以及当前的政治形势,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在相互影响。
对央行的指斥
要是事后分析就此打住,对于央行或许又过于仁慈了。毕竟,央行先前的所作所为让它们失去了回旋余地,且这不仅仅是出于上述原因。想想“财政主导”(央行采取行动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和“金融主导”(央行出于市场的缘由而采取默许的做法)的出现吧,它们显然与央行近年来采取的措施不无关系。
长期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拉高了资产价格和相关的杠杆作用,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部门都在加杠杆。诚然,这场疫情和普京发起的战争增加了政府支出,但长期的超低利率和被量化宽松等央行措施麻痹了的债券市场,也同样推高了政府支出。事实上,通过发行长期债券为专项政府支出融资,是有道理的。不过,清醒的经济学家们一面为支出摇旗呐喊,一面并没有告诫世人当心这些支出建议暗藏的陷阱;由于政坛分裂,立法机构唯一可以通过的支出法案,就是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法案。政客们一如既往地祭出信手拈来的不可靠理论(比如现代货币理论),有了这些理论,他们就像是拿到了执照,花起钱来毫无节制。
央行购买由隔夜储备金融资的政府债券,缩短了政府和央行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融资期限,这加剧了问题的复杂程度。这意味着随着利率的提高,政府财政可能出现更多问题,特别是在负债累累且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财政方面的考虑因素已经影响到了一些央行的政策,例如欧央行担心自身的货币政策对于(各国)“割裂”的影响——也即相对于财务状况良好的国家,财政状况疲软的国家的债务收益率飙升。央行可能至少应该认识到政治的性质正在改变,也即政府为应对冲击更有可能进行无节制的支出——哪怕是央行没有预见到冲击的到来。这样一来,压低长期利率、奉行长期低政策利率等做法或许会引起央行的更多关注。
私人部门也在加杠杆,家庭层面(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和企业层面莫不如是。但有一个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对流动性的依赖。由于美联储在量化宽松期间提供了大量的储备金,商业银行则主要通过大额活期存款为准备金融资,这就极大地缩短了债务期限。此外,为了让资产负债表上的大量低回报储备金产生收益,商业银行承诺为私人部门提供各种流动性——承诺信贷额度、投机头寸保证金支持等。
问题在于,当央行缩表时,商业银行难以在短期内迅速解除这些承诺,于是私人部门更加依赖央行获得持续的流动性。这个问题在2022年10月的英国养老金风波中初现端倪。英国央行出手干预,政府也放弃了庞大的支出计划,双方合力化解了这场风波。但此次事件表明,依赖流动性的私人部门可能会影响到央行缩表以收紧货币宽松政策的计划。
最后一点,资产价格高企引发了关于央行措施不对称的担忧:在经济活动放缓或资产价格下跌时,央行会迅速采取宽松政策;但在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同时带动经济活动过热时,央行却不愿加息。2002年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表示,美联储看不到资产价格暴涨的迹象,也无法阻止这种价格暴涨,但可以“在事情发生后减缓余波,并且有希望实现平稳过渡,进入下一轮经济扩张”。于是,“不对称”就成了美联储的一项政策圭臬。
资产价格高企、私人部门杠杆率偏高和流动性依赖,这些都表明央行可能面临着“金融主导”——左右货币政策的不是通胀水平,而是私人部门的金融形势。无论美联储是否愿意接受他人主导,私人部门目前都预测美联储即将被迫降息,这使得美联储取消货币宽松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要是没有私人部门的这种预期,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更严厉的政策立场。这意味着将给全球经济活动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其也意味着当资产价格达到新的平衡点时,家庭、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都将蒙受重大损失,它们都不是从价格上涨中受益的实体。由官僚机构管理的国家养老基金、涉世不深者和相对贫困的人会在资产价格飙升接近尾声时入场,这导致的分配结果,央行也负有一定责任。
而在政策外溢效应方面,储备货币国的央行政策会产生影响,而央行对此却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重要储备货币国的政策显然会通过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影响到其他国家。无论政策行动是否适合本国国情,其他国家的央行都必须做出反应,否则将面临资产价格上涨、过度借贷、最终陷入债务困境等长期后果。我会在结论部分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总之,央行虽可表示最近发生的事出乎它们的意料,但在限制其政策空间的问题上,央行自身也难辞其咎。它们政策的不对称性和非常规性,加之其表面上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已经触底的利率,引发了一系列失衡,不仅使得通胀更加难以控制,也使退出当前普遍实施的政策组合变得困难重重——即便是其通胀制度已经形成了极高的通胀环境。央行有时被说成是无辜的旁观者,但它们并不无辜,也不是旁观者。
偏离使命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央行官员非常清楚应如何应对高通胀,也有这方面的工具,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做自己分内的事。
不过,央行成功降低通胀之后,我们可能将跌回低速增长的状态。人口趋于老龄化,中国发展放缓,已成惊弓之鸟的世界正在走向军事化和去全球化,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央行官员不太了解低经济增速和低通胀的世界,他们在金融危机过后使用的量化宽松政策等工具,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此外,央行的激进措施还可能招致更多的“财政主导”和“金融主导”。
当一切恢复平静之后,央行的职能应是什么样的呢?央行的职能显然不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包容,它们通常没有处理这些问题的职能。央行应该耐心等待民选代表的授权,而不是在政治色彩浓厚的领域窃权。不过,授权央行在这些领域行事,算得上是明智的做法吗?首先,央行的工具在消除不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效果有限。其次,新的职责是否会影响央行履行其首要任务的有效性?例如,美联储的新框架要求关注包容问题,这是否会妨碍加息?因为在一轮经济扩张中,处境不利的少数群体通常(也很遗憾)是最后一批被雇佣的求职者。再者,这些新的职能是否会导致央行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政治压力,并引发新形式的央行冒险行为?这并不是说央行就不必担心气候变化或不平等问题给央行自身的明确任务造成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央行甚至可以遵循民选代表的明确指令(例如在进行市场干预时,买进绿色债券,放弃棕色债券),但央行会因此面临来自外部的微观管理风险。不过,直接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不平等的任务最好还是留给政府,而不是让央行负责。
央行在稳定物价方面的任务和框架又是怎样的呢?此前的讨论表明,各国央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矛盾。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央行需要一个框架——例如通胀目标制,即责成央行将通胀水平维持在某一区间内或是围绕某个特定目标均衡波动。但正如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经理奥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所言,低通胀环境与高通胀环境有很大区别。央行可能需要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框架。在低通胀环境下,无论价格冲击多么猛烈,通胀水平始终保持低位,央行要提高目前的通胀水平,就得更加宽容地对待今后的通胀。换言之,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话说,央行需要做到合理地不负责任。这意味着,央行采取的政策和框架严重束缚了自身的手脚,致使其在长期执行了宽松政策。但正如上文所述,放宽表面上的财政限制可能加速通胀环境的变化。
反之,在高通胀环境下,每一次价格冲击都会引发又一轮价格冲击,央行必须坚定不移地尽早消除通胀,它们此时的口号是:“等你看到通胀,就太晚了。”由此可见,在低通胀环境下因框架原因对于通胀的宽容,与高通胀环境下需要采取的措施是相悖的。但央行不能根据情况不同就随意改变做法,如果那样做了,央行的承诺就会失去效用。央行可能需要选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框架。
选择框架
要是这样的话,根据风险平衡原则,央行应再次强调其任务是利用利率政策等标准工具降低高通胀。假如通胀过低怎么办?我们或许应该学会与之共存,就像对待新冠病毒一样,同时避免使用量化宽松等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尚待确定、扭曲信贷、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并且很难退出的工具。可以这样说,只要低通胀不会发展到通缩螺旋,央行就不必过于担心。日本的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放缓,并非是由于持续了几十年的低通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才是罪魁祸首。
交给央行的任务过于复杂,不是一件好事;但央行可能需要得到更强有力的授权来协助维持金融稳定。首先,金融危机往往会导致央行难以应对的过低通胀。其次,正如我们所见,央行对待长期过低通胀的传统处理办法会推高资产价格,继而增加杠杆,还可能进一步引发金融不稳定。货币理论专家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维持金融稳定的最佳方式,但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奏效,主要经济体的房价过热就是明证。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于金融体系中的新兴领域以及与银行关系疏远的领域几乎不会产生影响,加密货币和模因股票的泡沫及破灭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对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系统以外的影子金融体系更好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但我们也应该记住,用杰里米•施泰因(Jeremy Stein)的话说,货币政策“无孔不入”。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吧!
央行政策造成的外部后果该由谁来负责呢?有意思的是,更多关注国内金融稳定的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溢出效应可能会更小一些。尽管如此,央行和学术界还是应该就溢出效应展开对话。各国央行官员在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定期会议,可以在这里启动非政治性对话。这一对话最终可转移到IMF,吸收政府代表和更多国家参与讨论在一体化的世界中该如何转变央行的职责。但在开展此类对话、就央行的使命达成政治共识之前,将央行工作重点重新放在降低高通胀的首要任务上,同时审慎处理维护金融稳定的次要任务,可能就够了。
这两项任务是否会让全球陷入低增长?不会,但会将推动经济增长的责任交还给私人部门和政府,这正是它们的职责所在。与当前的高通胀、高杠杆、低增长世界相比,突出重点、减少干预的央行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果。对于央行来说,确实是“少即是多”。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